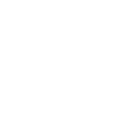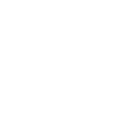平博体育规则,平博体育,平博真人,平博棋牌,平博彩票,平博电竞,平博百家乐,平博电子,平博游戏,平博体育官方网站,平博体育官网入口,平博体育网址,平博体育靠谱吗,平博体育app,平博app下载,平博投注,平博下注,平博官方网站,平博最新入口,平博体育平台推荐,平博体育平台赛事,平博赛事,平博在线体育博彩,平博足球博彩,平博足球投注,平博娱乐场西方哲学常被认为具有视觉中心主义的特征,实则是对象化视觉经验自古希腊起便影响着西方哲学的进程。与之相较,中国哲学自先秦便格外重视非对象化视觉经验,这在《庄子》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庄子》把人称作有眼睛的存在,体现了对视觉重要性的自觉,但观看没有被视作对所观的单向把握,而是被理解为与所观相契的一种行动。因此,《庄子》重视眼睛之间目光接触的视觉经验,坚持从感触的角度理解视觉的正面意义。与此同时,对视觉经验中对象化的一面,《庄子》则多加反思以警惕其中的危险与限度,尤其主张在生存论上抛弃主体性凝视并在认识论上克服形式化、视角性等视觉认知的限度。此外,光亮是视觉展开的必要条件,出于抑制对象化视觉经验的旨趣,《庄子》反对“光耀”而主张“葆光”,并以“玄冥”为理想的生存与观看之境,这与柏拉图的洞穴喻形成了鲜明对比。整体来看,《庄子》的视觉经验深刻影响了《庄子》哲学义理的展开与思想品格的塑造,从视觉经验的角度切入,《庄子》哲学的内在精义与独特性将能获得基源性理解,而这对从经验出发的中国哲学研究也具有示范意义。
在现代研究中,西方哲学与视觉经验的关系得到了充分关注。论者多指出西方自古希腊起根植于视觉经验形成了视觉中心主义的传统,而现代哲人如伽达默尔、梅洛-庞蒂等为克服视觉中心主义,不断挖掘听觉、触觉等感官经验之于哲学的意义。然而,在批判视觉霸权的现代思潮中,视觉本身的多面性并没有得到充分揭示。例如,研究者多按照探照灯工作的样式理解视觉,观看被视作观看者对观看对象的单向把握,相较而言,触觉则通常被理解为具有触即被触的交互性、双向性,这种“双重感觉”构成了现代哲人克服视觉中心论的重要依据。但诸感官知觉并非隔绝不通,通常被标识为某一感官的知觉特性只是该感官的主要特征或典范特征,而非全部特征。就触觉而言,交互性的触觉感知最典范地体现在肌肤之间的感触,而当用手触摸形状分明的静物如石块时,触觉便扮演着视觉式的单向认识对象的功能。与之相应,视觉感知不仅具有单向性、对象化的一面,同样也具有触觉式的交互性、非对象化的一面。前一方面主要体现在人们观看静物的视觉经验中,此时客体不对眼睛有精神层面的作用,我们只是单向地把握作为对象的客体;但在我们与他人的眼神相互接触的视觉经验中,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此时看即被看,亦即我们在观看他人之际他人也在观看我们,并且我们如何观看他人本身也构成了他人观看我们的一部分。
对视觉感知不同特征的分殊,有助于我们明确视觉中心主义所建基其上的视觉经验仅仅是视觉经验中单向性、对象化的一面,西方哲学根深蒂固的现象与实在二分的形上学、旁观式的认识论等成见正与此密切相关,而视觉经验中非对象化的一面则始终没有在西方传统中取得足够重视。与西方相较,在传统中国,虽然对象性视觉经验在先秦、魏晋、明清之际等时段受到了一定重视,但整体上哲人、思想家不太重视眼睛之于把握对象之形式的功能,而是重视眼睛之于传达人之内在情实的意义,并由之贬抑旁观式的观看之法,注重相视的视觉经验。如果能够充分呈现传统中国对视觉经验的独特理解,中国哲学的特质将能够在感官知觉层面获得基源性理解。不过,由于这一话题涉及的文献众多、线索纷繁,在整体研究之前需要充分的个案研究。基于此,本文以《庄子》为中心,探究《庄子》的视觉经验及其哲学效应,借此展现由基础生存经验出发而达乎哲学内在义理以及中国哲学之特质的研究进路。而之所以选择《庄子》,原因有二:其一,中国哲学对视觉经验的独特理解肇端于先秦,并在诸子时代得到了理论探究,对《庄子》视觉经验的研究具有源头意义;其二,在诸子哲学中,《庄子》对视觉经验的讨论最具典范性,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充分展现了对非对象化感知的自觉。
《庄子》对眼睛的重要性有充分自觉,这体现在其把人称作有眼睛的存在。在《天地》篇,苑风对谆芒说:“夫子无意于横目之民乎?愿闻圣治。”“横目之民”指百姓,而以“横目”界定百姓乃是对商周思想的继承与反叛。商周时期,眼睛之于人的重要性已经凸显出来,这由甲骨文、金文“民”“臣”二字的字形可见一斑。“民”之初义为虏获的奴隶,主人将其刺瞎一眼以示区分,是以甲骨文、金文“民”作“天”“民”,像一利器插入眼睛之中。“臣”字初义为奴仆,甲骨文、金文作“地”“臣”,像奴仆于主人前低头时眼睛竖立之状。由“民”“臣”的字形来看,在商周观念中,主人占有奴隶体现在对奴隶眼睛的合法剥夺,奴仆臣服于主人则被理解为眼睛的臣服。不难发现,眼睛在商周时代已经被看作精神性器官,《庄子》以眼睛的状态界定百姓即是对商周观念的继承。不过,“臣”字造形为“竖目”之状,《庄子》却把百姓称作“横目之民”,这便体现了对商周观念的反叛。在《庄子》看来,百姓并非下跪低头供圣人侧视,而是与圣人面对面平等互视。因此,百姓的眼睛由“竖”变“横”,百姓与圣人的关系也就由主奴式的关系变为平等共在的关系。
如果说《天地》“横目之民”的讲法侧重于从政治角度突出眼睛的意义,那么《田子方》“有目有趾”之说则在生存论上赋予了眼睛以优先地位。在《田子方》篇,仲尼对颜回说:“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万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后成功。”“有目有趾”代指人,马叙伦说:“‘目’当依《天地》篇作‘首’。”《天地》云:“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众,有形者与无形无状而皆存者尽无。”马叙伦依《天地》改《田子方》固然使两者取得了形式上的一致,却也错失了《田子方》“有目有趾”的意蕴。从两者的上下文来看,其旨趣并不一致,《天地》“有首有趾”突出了人之形体的一面,对应的是该篇下文的“有形者”,而在《田子方》中,颜回在上文自述“及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者”,“奔”“瞠”正涉及脚与目,是以仲尼以“有目有趾”回答。从更内在的义理来看,当《田子方》以“有目”亦即有眼睛的存在来界定人的时候,其所突出的是眼睛在诸感官中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因此,《田子方》“有目”并非《天地》“有首”之误,而应当看作《天地》“有首”的一个更具体的讲法,即在“首”所具有的眼耳鼻舌中,眼睛特殊而重要。
以眼睛来界定人,不唯《庄子》如此,柏拉图对话中亦常见类似讲法。例如,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把眼睛称作人身体上最美的部分,并把视觉看作人所具有的最宝贵的感知能力。在《克拉提洛斯》篇,苏格拉底把人定义为在一切动物中唯独可以“察看所见之物者”。在自然界,有眼睛并可以观察的动物并非只有人,那为何《庄子》与柏拉图分别以“有目”与“查看所见之物”来界定人?换言之,眼睛的独特性体现在哪里?对此,亚里士多德有一个经典的解释。在《形而上学》开篇,亚里士多德谈到:“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即使并无实用,人们总爱好感觉,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较之其他感觉,我们都特爱观看。理由是:能使我们识知事物,并显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此于五官之中,以得于视觉者为多。”亚里士多德从视觉之于求知的意义的角度赋予视觉以优先性,这种做法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杜威即指出,“认识论是仿照假设中的视觉动作的模式而构成的。……实在的对象固定不变,高高在上,好像是任何观光的心灵都可以瞻仰的帝王一样。结果就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旁观式的认识论”。在旁观式认识论所建基其上的视觉模型中,光线对眼睛的影响是生理机制上的影响,对象让观者发生的变化只是让观者获得认识对象的可能,而在整个认识过程中,心灵与对象始终是相分离的状态。
与亚里士多德相较,《庄子》虽然同样重视眼睛及其观看功能,但其所重视的观看并非旁观,在上引《田子方》“有目有趾者”的表述中,“目”的意义并非旁观太阳并由之获得关于太阳的知识,而是追随运动着的太阳,从而获得一种堪称“成功”亦即合乎道的生存。进而,在眼睛对太阳的追随中,目光始终与太阳粘连在一起,而不与之分离。与此同时,太阳也并非独立自存而与人无关的客体,它始终引领着观看者的目光,让观者随着它的出入或劳作或休息。因此,在这种类别的观看中,观看并非对观看对象的单向把握,所观在观看行为中呈现出精神性的意义,进而以此意义引领着观看者与之相合。
这个寓言刻画了一种观看活动。首先,支离叔、滑介叔所观看的并非事物的形式化特征,而是作为整体的万物生死、天地运化,此即“观化”。其次,在“观化”活动中,观者寓于所观,所观不离观者。成玄英解“柳生其左肘”云:“柳者,易生之木;木者,棺椁之象。此是将死之征也。”大体来看,“柳生其左肘”如同《大宗师》“化予之左臂以为鸡”“化予之右臂以为弹”“化予之尻以为轮”等讲法,指滑介叔处于生死物化之际。在该寓言中,这种物化是滑介叔的所观,而滑介叔正处于所观中,“观化而化及我”的表述正道出了这一点,即“我”本身就在“化”中,观者与所观交织为一整体而不相分离。因此,支离叔与滑介叔在冥伯之丘的“观”并非旁观式的认识活动,所要获得的也不是亚里士多德情有独钟的“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而是对天地万物死生交替而呈现出的“生者,假借也”以及“死生为昼夜”的领会。这种领会指引着观者的生存姿态,滑介叔以淡然无恶的态度面对左肘生柳这一变化正是获得该领会的表现。
观看并非对所观的单向把握,而是与所观相契的一种行动,而在视觉经验中,相视最能展现观看的相契特征。《天运》云:“夫白鶂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眸子不运”即目不转睛地看,这不是带有权力欲的凝视,而是深情的注视,唯其如此,才可“风化”。王先谦云:“‘风’读如‘马牛其风’之‘风’,谓雌雄相诱也。‘化’者,感而成孕。”目视而成孕的讲法属于古时的知识系统,《庄子》借此所道出的是:眼睛之间互相深情注视超越了单纯观看的范畴,相视中目光的交接如同身体间的相互触摸,能够打破隔膜实现感通,一定程度上具有肌肤相亲的功效。实际上,目光间的感触穿透身体直入心灵,无论能否产生肉身交合的效用,无疑的是它能实现相视者幽微而深刻的精神沟通。《大宗师》论子祀等朋友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又论子桑户等朋友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友”。朋友之间心意相通,在目光感触性的交接中,便足以深入对方心灵,获得最厚实的领会。
在《庄子》的思想世界中,相视而深交的行为被视作大道的体现,并且被认为是得道者才有的境界。《田子方》载仲尼见温伯雪子而不言,子路问其故,仲尼云:“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若夫人者”意味着凡人不可“目击而道存”,必得道者而后可。“击”即击打,指快速、强烈并且会产生内在震动的触碰。在这个语境中,“目击”强调的是仲尼与温伯雪子两人虽然快速触碰了对方的目光,但两人却已然能够深入地领会对方的心灵,尤其是仲尼领会了温伯雪子的合乎道的精神世界。仲尼强调,这种领会直入心灵最深处,因此“亦不可以容声矣”。声音、语言本是存在者克服距离的中介,但仲尼指出,目光的感触足以实现心灵的深层领会以及对道的体认,此时声音、语言等中介性的工具反而会成为某种障碍,因而不再是必要的。

综上所论,在对商周观念的继承与超越中,《庄子》把百姓称作“横目之民”,把人称作“有目”者,显示了对眼睛之于人的重要性的重视。不过,当《庄子》以眼睛来界定人时,其所重视的并非旁观式的视觉经验,而是面对面相视、目击的视觉经验。对《庄子》而言,眼睛的功能并非与他者拉开距离并将之对象化,而是或追随运化着的天地万物、或与同样有眼睛的他者实现目光的交接,无论如何,其所追寻的是与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的深度相契。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诸感官中区分视觉并赋予视觉以优先性相较,《庄子》中的眼睛自始就与感触相联系。换言之,《庄子》始终是从感触的角度去理解视觉的正面意义,而对视觉中单向性与对象化的一面则多加警惕与反思。
《应帝王》末章载,儵与忽为浑沌日凿一窍,七日而七窍成,七窍成而浑沌死。对这个寓言,可做两方面解读。其一,诸感官是危险的存在,它们对浑沌之死即本源性生存状态的失落承担责任。其二,在该寓言“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的表述中,“视”在“听”“食”“息”之前,对后三者有着虽幽微但不可忽视的统领作用。两方面结合,可以做出如下推论:视觉在诸感官中对浑沌之死承担着更多的责任,亦即诸感官的危险性首要的是视觉的危险性。在《庄子》中,视觉的危险性主要和对象化的凝视行为相关。《人间世》载匠石观栎社树而以其为无用,栎社树见梦云:“且也若与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几死之散人,又恶知散木!”“相物”即通过对象化的观察、审视以判断该物是否有用。在匠石之“相”中,栎社树的精神性被剥落,它只能作为工具而非目的,只能被宰制而不能有自身的意义。《庄子》借栎社树之口谈到“若与予也皆物”,此即向世人指出观者与所观在价值上同等,不能通过“相”对万物赋值,而“几死之散人”之说则是警告世人“相”的凝视不仅会伤害所相,而且最终会损害相者。
“相”之所以会损害相者,原因在于:当万物皆沦为人可资利用的对象,以视觉为首的诸感官将进一步宰制对象以满足欲望。《至乐》云:“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目欲好色,耳欲音声,目与耳若不得其所欲,则身心忧惧,忧惧则会损伤身心。因此,对形体与心灵的养护来说,目与耳等感官的欲望产生了巨大的危险。《庄子》对此多有刻画,《天地》云:“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五色、五声等人之所欲不仅使目与耳等感官不明、不聪,更会导致人之本性的损害。因此,世人所推崇的离朱之明、师旷之聪就成了批判的对象,《胠箧》云:“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在另一些篇章中,《庄子》将矛头直指耳目等感官,如《德充符》之“寓六骸,象耳目”,《大宗师》之“忘其肝胆,遗其耳目”以及“堕肢体,黜聪明”,《在宥》之“堕尔形体,吐尔聪明”,等等。“遗其耳目”等并非在肉体上胶目塞耳,而是要“剔除耳目之欲,遗忘耳目之欲,使耳目之欲与耳目之官能分开”,只有耳目解脱对声色的欲望,视听等感官才能恢复到不被遮蔽的本真状态,人也才能恢复被声色损伤的本性。
在生存上,以视觉为首的诸感官存在危险;在认识上,视听等感官则存在限度。《天道》云:“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形色名声是事物的属性,这四者需要主体与客体拉开距离观看、倾听而后得。《庄子》主张,仅仅把握形色名声不足以穷尽事物的情实,其实质是不以形色名声为事物的本质规定,并由此拒绝以视觉、听觉为代表的对象化进入事物的方式。《骈拇》云:“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庄子》区分了两种“明”与“聪”。一种以离朱、师旷为代表,他们长于分辨五色、五声,即将整全的色、声对象化并加以分辨,所谓善于“闻彼”“见彼”,“彼”意指对象化的他者。另一种则表现为克服了感官向外追寻的功能,进而“自闻”“自见”,即将视听等感官知觉收归自身。《人间世》云:“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内通”即不再向外追逐,进而专注于向内的倾听与省察。“外于心知”,成玄英云:“忘外于心知。”即拒斥心灵“闻彼”“见彼”式的求知进路。在《庄子》看来,如果能够拒斥耳目、心灵对象化地向外求索,那么鬼神将会舍止人身而他人也会归依于此,亦即修道者将实现与物为一的存在状态。
《天道》等篇视听并提,但两者相较,听觉虽依赖距离并具有对象化的特征,但倾听本身是为了通过声音克服听者与所听的距离。视觉则不然,在对象化的观看中,距离始终要得到保持,唯其如此才能使所观确立为对象,进而使主体得以旁观式地探究。因此,相比于听觉,视觉的对象性更强,《庄子》也更加注重对视觉的克服。《养生主》载庖丁云:“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面对牛,视觉仅能把握形色,而无法通达肌理。庖丁最初以视觉对待牛,所见只是一头浑全之牛而已;三年之后稍有进境,不再纯依视觉,故不再见全牛;最终完全克服视觉而依靠精神,此时便能切入牛之肌理而游刃有余。庖丁云:“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视为止”再次强调了对视觉的克服,而“见其难为”之“见”义同于“知”,庖丁并非看见了难以下刀处,而是牛的筋骨交接处通过刀而传达至手,庖丁由此感知。从“所见无非牛”到“未尝见全牛”再到“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以及“见其难为”,庖丁由“技”进“道”的过程正是不断突破视觉的过程。对庖丁而言,视觉认知把事物当作外在对象,无法进入事物内部,而解牛活动恰恰需要进入牛的内部而与之相契为一,是以克服视觉式的认知方式就成为庖丁所必经之途。
进一步来看,视觉认知还有视角性的特点,即观看总是立足于某处的观看,视觉对象不能一次性全面呈现,而是总会受到观看视角的影响。《庄子》承接《老子》对此多有讨论,《齐物论》云:“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德充符》云:“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秋水》云:“夫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同一物在不同观者甚至同一观者的不同视角下所显示的状态并不相同,由此可以得出如下推论:修道者为了获得关于事物的全面认知,应不断切换视角以避免单一视角的片面。实际上,《庄子》就是这么做的,其多数篇章都在开辟视角,为世人提供理解世界的不同视域,从而破除诸多成见。然而,如果所有视角都只能提供有限认知,那么无论如何切换视角,都不能得到关于事物的全面认知。换言之,如果所有视角下的认知都是有缺陷的,那么无论如何叠加视角,都无法使最后的认知真切无妄。归根结底,视角性是视觉认知的特点,就真切领会事物而言,视角性是应当加以克服的局限。
这段文字列举了六种“观”,在每一种“观”中,物都呈现出不同的规定,这无疑体现了《庄子》转换视角的努力。然而,这六种“观”并不具有同等的位置。“物无贵贱”是“以道观之”所得的对万物的见解,在《庄子》中,这是对万物最真切的领会。因此,“道”是《庄子》式的真人、至人领会天地的出发点。与之不同,“物”“俗”“差”“功”“趣”则是世人认识万物的立足点,“自贵而相贱”“贵贱不在己”等皆是世人的偏执,而非世界的本然样态。更为重要的是,“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等五种观法及所观到的状态必立足于“以道观之”而后可。换言之,世人沉溺于“物”“俗”等视点,本身无法跳脱“自贵而相贱”“贵贱不在己”等认知状态,更无法对之进行批判性反思,而当《秋水》道出“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之际,其已经立足于“道”并基于“道”来审视“物”“俗”等视点了。因此,“以道观之”卓然不同于其余五种观法,《庄子》列举后五种观法,并非令世人停留其中,而是为了揭示其中的虚妄并加以抛弃,最终获得“以道观之”的视域。
在“道”的视域下,万物不再以有所偏蔽的状态显现,而是显示其本真状态。《秋水》云:“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无拘而志,与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谓谢施,无一而行,与道参差。”成玄英云:“反衍,犹反复也。夫贵贱者,生乎妄执也。今以虚通之理照之,则贵者反贱而贱者复贵,故谓之反衍也。”又云:“谢,代也。施,用也。夫物或聚少以成多,或散多以为少,故施用代谢,无常定也。”“道”超克了诸视角的偏执与虚妄,“以道观之”虽仍用了“观”字却已经超出了视觉认知的范畴。因此,“反衍”“谢施”并非世界诸形态中仍有偏执而不得真切的形态,对“反衍”“谢施”的领会也并非诸多俗见之一,相反,这是天地万物最真切的形态,修道者以对这种状态的领会以及在该领会引领下生存为最终追求。

综上所论,对《庄子》而言,以视觉为首的诸感官的危险主要源于将万物对象化并以有用性加以宰制的凝视行为,进而表现为诸感官对万物的欲求以及该欲求对人之本性的伤害;视觉的限度首要地表现为视觉认知只能把握事物的外在形色而不能通达内在肌理,进而表现为视觉认知的视角性不能获得关于事物全面而真切的领会。因此,《庄子》警惕视觉的危险与限度,并为克服视觉提出了“不以目视”“以道观之”等命题。值得再次指出的是,本节对视觉的批判皆就视觉的对象化一面而言,这些内容和上节讨论的《庄子》对非对象性视觉经验的重视与发掘一体两面,共同构成了《庄子》对视觉经验的整体态度。
以旁观、互视为两种观看典范,视觉经验可分为单向性与交互性或对象性与非对象性两类。在这两类观看中,光亮都是必要条件,但两者对光亮的要求并不一样:前者要求充分的亮度,如实验、手术等活动对灯光有着严格的要求,以便对象清楚地展现出来;后者则不然,互视的实现只需要有光即可,而且如果亮度格外强烈,目光便很难有效接触。这种不同的光亮经验在哲学上也有表现,如在推崇视觉的柏拉图哲学中,真实的观看应该在太阳之下而非洞穴之中,洞穴与太阳、意见与真理由此相互对立。相比于柏拉图,《庄子》的情况较为复杂。一方面,由于拒斥对象性观看,《庄子》对“光”保持着警惕,但另一方面,由于并不完全排斥视觉,《庄子》又不会遁入绝对暗黑。在《庄子》中,对光亮的复杂态度具体表现为光明与玄冥之辨。
从思想渊源来看,《庄子》对“光”的警惕源于《老子》。《老子》云:“光而不耀。”(第58章)“耀”是“光”向外闪烁的状态,“不耀”即反对光芒四射之状。与此相应,《老子》主张“和其光”(第4、56章),即令“光”柔和而不强烈。《庄子》承接了《老子》如上精神,如《刻意》有“光矣而不耀”之语;《知北游》以“光耀”命名寓言的主人公,此人问乎无有而不得其问;在《天地》中,黄帝“南望”而“遗其玄珠”,“南望”即向光明处远望,正是这种远望,玄珠遗丧。凡此皆表明了《庄子》对阳光照耀状态的自觉拒斥,这种拒斥与柏拉图走出洞穴的比喻无疑形成了鲜明对比。再者,《齐物论》云:“是故滑疑之耀,圣人之所鄙也。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在《齐物论》的语境中,“滑疑之耀”指形名家坚白之论,这种对万物所进行的形名之思是视觉性思维方式的重要表现,《齐物论》以“耀”对之刻画正突出其视觉性,而将之称作“滑疑”则强调名辩诸家的形名之思惑乱人心而非真知,因而,视觉性的思维方式为圣人所鄙弃。
拒斥“光”之“耀”,并不意味着全面“光”,“光矣而不耀”之说便表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在纯粹的暗黑中,无所观亦无所见。因此,《齐物论》在鄙弃“滑疑之耀”的同时主张“以明”,《庚桑楚》也在正面意义上谈到“天光”,其云:“宇泰定者,发乎天光。发乎天光者,人见其人,物见其物。”胡文英云:“心胸泰定,则发天然之光耀,而照见真吾。”真实自我的显现需要“光”“明”,这一隐喻式的表达显示出《庄子》虽然光芒照耀的状态,但并非陷入暗黑之断灭。此外,《庄子》为了克服“光”之“耀”经常在正面意义上使用“玄”“冥”“幽”“昏”“昧”等词,这些词皆非光芒普照,但也并非一片漆黑。例如,“玄”本义为赤黑色,《说文》云:“黑而有赤色者为玄。”“黑”表示无光,“有赤”则表示并非纯黑。要之,“玄”“冥”等词的使用同样表明了《庄子》并非要遁入无光亮、不观看的存在境地。
《刻意》《知北游》拒斥“耀”“光耀”,《齐物论》《庚桑楚》主张“以明”“天光”,后者的“光”“明”何以不同于前者的“光耀”。一般认为,驱散黑暗的光亮总是显示出神圣性与崇高性。“上帝说:光!就有了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些光的隐喻中,上帝与孔子都是神圣的崇高者。但在《庄子》中,“天光”虽以“天”为规定,但并非高高在上、远离凡常,相反它始终关联着大地与庸常。《田子方》云:“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高亨说:“疑原作‘肃肃出乎地,赫赫发乎天’,‘天’‘地’二字转写误倒。阴出于地,阳发于天,理不可易。”高亨以世俗观念来纠正《庄子》文本,恰恰忽视了《庄子》对世俗观念的颠倒。常识看来,至阳出于天,至阴出于地,但在《田子方》的表述中,幽昏出自天空,光明出自土地,天与地、幽与明相互交织,由此幽昏具有天空性而光明也具有了大地性。再者,在《齐物论》与《庚桑楚》中,“以明”“天光”都连接着“庸”,所谓“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齐物论》),“行乎无名者,唯庸有光”(《庚桑楚》)。陆西星云:“寓诸庸者,因人之是也。盖无物不可,无物不然,故庸众之中皆至理之所寓。”宣颖云:“去私见而同于寻常。”“庸”即庸常、平常,指向的是日常生活世界。综合来看,《庄子》中的“光”“明”具有大地性并显现于庸常。不同于向外照射的“光耀”,“光”“明”的大地性使得它具有收摄遮蔽的意蕴,故《齐物论》有“葆光”之说。“葆光”与“以明”是同一旨趣的两个说法,成玄英云:“葆,蔽也。……韬蔽其光,其光弥朗。”“韬蔽其光”的“光”是光耀,“其光弥朗”的“光”是光明,唯有“葆光”才能“以明”。
《庄子》所肯定的“光”“明”生发于大地并寄寓于庸常,这种“光”“明”不是为视觉认识提供可能的必要条件,而是生存论意义上的敞亮之所。《逍遥游》对大樗树的安置是“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逍遥者不会直接暴露在天地之间,大樗树为他提供了具体的游息之地,它不仅使得逍遥者在无所有之中又有所伴,同时遮蔽了阳光而为其提供了阴翳。彷徨于大樗树下的逍遥者并不直接面对光耀,也不陷入暗黑,他在树影斑驳之中,处于光耀与暗黑之间。换言之,逍遥者既在光明之中,亦在玄冥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光明”与“玄冥”是同一状态的不同讲法。从近于光耀来说是光明,从近于暗黑来说是玄冥。若强调光明,侧重的是对暗黑的去除,若强调玄冥,侧重的是对光耀的抑制。
不过,虽然一定语境下,“光明”与“玄冥”指同一状态,但两者不可完全等同。在《在宥》篇,广成子对黄帝说:“吾语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我为女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女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至道”之中包括“大明”与“窈冥”、“至阳”与“至阴”两个层面,但广成子对“至道”的直接刻画是“窈窈冥冥”“昏昏默默”,这强调了幽昏无声乃是大道的本质特征。在《知北游》首章,知三次问道于无为谓、狂屈与黄帝,其场景分别为:“知北游于玄水之上,登隐弅之丘,而适遭无为谓焉”;“知不得问,反于白水之南,登狐阕之丘,而睹狂屈焉”;“知不得问,反于帝宫,见黄帝而问焉”。“玄水”“白水”“帝宫”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从幽昏处不断向明亮处转进的过程,“遭”“睹”“见”同样形成对比,这是视觉不断展开、不断张扬的过程,最初仅是身体上的遭遇,最后则成了眼睛上的明见。在该寓言的刻画中,向明亮处转进与视觉的张扬是同一过程,而这一过程亦是不断偏离道的过程。不过,还值得注意的是,知对道的领会又恰恰是在这种偏离中实现的。这里的关键是知尚未达至光芒四射之境,身处帝宫的黄帝仍可自我批评,而在黄帝“我与汝终不近也”的反思中,其所展现的正是由“帝宫”重返“玄水”的旨趣。
综合上引《在宥》与《知北游》的两个寓言可见,《庄子》虽重视“光”“明”,但“玄冥”更具有根基性。《知北游》明确谈到:“昭昭生于冥冥。”这即是强调,“光”“明”从“玄冥”之处来,“玄冥”为“光”“明”奠基。《知北游》又云:“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于人之论者,谓之冥冥,所以论道,而非道也。”在这里,“冥”兼指视觉与听觉,但以“冥”这一视觉语词来统称“无形”“无声”无疑侧重视觉层面。《庄子》提醒世人“冥”不可替代“道”,但能以“冥”论“道”则显示出两者具有内在关联。从根本上说,《庄子》把“冥”看作天地的本然色调。在《逍遥游》中,大鹏自北冥背负青天而迁徙于南冥,北冥与南冥皆称之为“冥”表明两者皆呈幽昏之色,而“冥”字又与表天空之深青色的“苍”字共同凸显了鲲鹏生存之域的幽昧特征。依《庄子》,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的理想生存之境与观看之境皆是“冥”,《天运》云:“动于无方,居于窈冥;或谓之死,或谓之生;或谓之实,或谓之荣。”《天地》云:“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冥”中仍可“见”,仍有“晓”,但“冥”之幽昏不同于“光”之明亮。在明亮中,一切皆清晰可见,在幽昏中,一切形式皆模糊不清。因此,在“冥”中观看,不再以形式为事物的本质,在“冥”中生存,也不再以形式化的准则来要求自身,这既是《天运》“动乎无方”的旨趣,也是上节所论《庄子》不以“形色名声”为事物本质的又一体现。
以上探究揭示了《庄子》对交互性、非对象化视觉经验的重视,对单向性、对象化视觉经验的反思,以及在光明与玄冥之辨中偏重后者的倾向。进一步应当追问的是,《庄子》的这些态度对其哲学产生了什么样的效应。在上文中这一问题已有所涉及,尤其是第二节从反面呈现了《庄子》在认识论与生存论上不主张什么,本节将继续讨论与独特视觉经验相交织的《庄子》哲学的正面主张。而为达此目的,需要再次深入分析《庄子》中的“形”。上文谈到,《庄子》不以“形色名声”为事物的本质特征,而综观《庄子》,在“形色名声”四者中,《庄子》对作为视觉对象的“形”进行了更全面的讨论,正是在这些讨论中,《庄子》的正面主张得到了具体呈现。
在《庄子》中,“形”主要指形状、形象,并尤其突出形式的含义,如《德充符》“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大宗师》“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等等。“道”“德”没有形状、形象,更重要的是,它们没有形式化规定。在《庄子》看来,“形”是万物的属性,创生万物的大道“无形”。大道为万物奠基,“无形”比“形”更为根本。《天道》云:“故《书》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庄子》并不否定“形”以及基于“形”的“名”的存在,但“非所以先”“不知其本”之说在存在论上赋予了“无形”之“道”以优先性。进而,《庄子》把“道”称作使“形”得以可能的存在。《大宗师》论“道”云:“吾师乎!吾师乎!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知北游》亦云:“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刻雕众形”与“形形”含义相同,都强调“道”为“形”奠基,是以真人、至人师法“道”而不执着“形”。

以“道”超越“形”的存在论为《庄子》克服形式化的道德与政治奠定了基础。首先,在德性论上,《庄子》区分了两种“德”。一种是合道之德,《庄子》称之为“道德”,此“德”至高至深且完备无缺,故也称为“至德”“全德”。另一种则是形式化道德,它们由合道之德拆分而成,具体表现为“仁”“义”等具体德目。《马蹄》云:“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在《庄子》中,“毁道德”的内涵是使“道德”成“形”。《天道》云:“形德仁义,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宣颖云:“形其德于仁义,乃神明之绪余耳,世俗鲜不为末学所惑。”“形德仁义”意为使“德”成“形”而渐有“仁”“义”之称,世人仅以“仁”“义”为“德”,殊不知此乃“形德”之后的产物而非“不形”之“德”,而“不形”之“德”正是《庄子》所谓的“全德”。《德充符》以哀骀它为“全德之人”,他的表现正是“德不形”,其云:“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平静的水面没有纹路可寻,动荡则有波痕、水浪。《庄子》以平水为喻,所突出的是内有其德而德不外显,尤其是不以形式化的方式外显的存在状态,而这种反对形式化道德而复归合道之德的德性论正建基于超克“形”的存在论之上。
《庄子》的德性论与政治观密切关联,其中一个典型表现是合道之德的失落被刻画为历史性的政治演进。《缮性》云:“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混芒”“澹漠”之际,无为而自然,社会政治没有形式规定。然而,在“德下衰”与圣人“为天下”的过程中,一切都被赋予了“形”,“散朴”“离道”“附之以文”正是对社会政治不断形式化的刻画。从这个角度看,“为天下”以赋“形”为内涵,相应地,《庄子》主张的“无为”便以去除天下之“形”为内在要求。因此,对战国时努力将社会形式化的形名家,《庄子》多有批评。《天道》云:“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谓辩士,一曲之人也。”治天下以大道为根基,形名赏罚仅是治具而非治道。然而,大道以“无形”为特征,治道与治具有内在冲突。对这一冲突,《庄子》提出了“不得已”的概念,《在宥》云:“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君子治天下乃不得已,但即使如此,也需要以“无为”为根本精神。归根结底,在治道与治具之间,《庄子》青睐治道,即使不得已施展治具,也要以治道为最终依托。
进一步来看,《庄子》中的“形”在形式义外还有形体义,如《齐物论》“形固可使如槁木”,《德充符》“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等等。《庄子》对形体之“形”的态度与对形式之“形”的态度一脉相承。一方面,《庄子》肯定“存形”“养形”的重要性,“存形穷生”(《天地》)、“养形必先之以物”(《达生》)等表述皆传达了这一点。但另一方面,《庄子》极具洞察力地指出,存养形体并不足以达乎生命的根本,《德充符》载仲尼云:“丘也,尝使于楚矣,适见㹠子食于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弃之而走。不见己焉尔,不得类焉尔。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母猪死后,小猪不久就会离开,这是因为小猪无法在母亲的形体中“见己”“得类”,即形体并非自我、类属的根本规定。因此,《庄子》常以“离形去知”(《大宗师》)、“形体掘若槁木”(《田子方》)等表述刻画理想人物。在《庄子》看来,真正规定“己”“类”的并非“形”而是“使其形者”,而“使其形者”常被刻画为“道”“精”“神”。例如,《天地》云:“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在宥》云:“抱神以静,形将自正。”《知北游》云:“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根据《知北游》的谱系,“精”“神”为“形”奠基,但“道”又为“精”“神”奠基。因此,究极言之,真正的“使其形者”乃是“道”。不过,“精”“神”等概念并非思想赘余,《刻意》论养生,一则批评“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的“养形之人”,一则指出“圣人贵精”以及“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惔而无为,动而以天行”的“养神之道”。正是“精”“神”等概念的提出,使得“道”在生存论上得以具体化,亦即“精”“神”等概念为存养生命提供了具体的着手点。
从根本上来说,“形”无论是形式还是形体,都是视觉对象,亦即都是事物呈现于外的对象化特征,是以《庄子》在形式与形体两方面都主张以“道”超越“形”。而作为对“形”的超克,“道”不再是视觉对象,也就不能用对象化的视觉认知的方式加以把握。那么,如何领会、通达“道”呢?就此,《庄子》提出了“体”的方法。《应帝王》云:“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天地》云:“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刻意》云:“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山木》云:“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体尽无穷”“体性抱神”“能体纯素”“晏然体逝”皆“体道”之别称,《知北游》更直接道出了“体道”的概念,其云:“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今于道,秋豪之端,万分未得处一焉,而犹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体道者乎!”“体道”意味着“道”可“体”,而作为方法的“体”,其所强调的是“物我彼此融合,展现出两体之间的距离消弭、彼此交融之方法论内涵”。去除与他者的距离并与之交融,这种“体”需要亲身进入事物之中,而不是远远观望事物的表象,耿宁指出:“‘体’意味着身体躯体(Leibkörper),而所有这些表达(引按:指‘体认’‘体会’‘体验’等词)都意味一种通过自己经验的‘体现’(Verkörperung)而对某物的认识或理解,并且可以通过‘亲身的经验’‘通过自己的生活的理解’‘通过向自己实践中的换位来认识’而得到再现。”在《庄子》中,修道者所要“体”的是“道”,而由于大道“无所不在”而“无乎逃物”(《知北游》),所以修道者通过“体物”的方式来“体道”。《庄子》中的技艺寓言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等正昭示了这种进路:通过对万物质实的体会、对与物交接过程情实的体验,最终完成对“道”的体认。概言之,在《庄子》视域中,“道”可以并且应该“体”,正是“体”的提出,使得《庄子》确立了不同于对象性视觉认知的方法论基础。
“道”不可以用对象化的方式加以把握,体道者的眼睛亦非对象化把握客体的眼睛。《马蹄》刻画至德之世的民众,其云:“其行填填,其视颠颠。”王敔云:“颠颠,专一也,目不游也。”“目不游”即《天运》的“眸子不运”,强调的是观看者目光专一而不游移。这种注视不是让观者充满欲望地占有万物,而是让观者从不切身的事物中解放出来。《知北游》载捶钩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其自述云:“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钩,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捶钩用眼而不耗眼,反而可以锻造一双明亮的眼睛,其关键是捶钩者自觉地将目光停留在所观,而不在其余事物上损耗目光。将目光停留在所观,所追寻的是与所观的相契,这种非对象化的观看与“体”所强调的两者之间的交融内在贯通,它是修道者“体物”“体人”乃至“体道”的方式,也是体道者本身的观看方式。
始终停留在切身处的目光不具有自然科学式的认知功能,但却是保持初始生命力的内在要求。因此,《庄子》不似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始终以成人的眼睛为设想,而是赞叹婴儿、牛犊的目光。《庚桑楚》云:“儿子终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终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终日视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释文》云:“瞚,字又作瞬,动也。”“目不瞚”即目光不会弥漫游荡,这种目光不会对所观看的外物有所偏向,是谓“偏不在外也”,宣颖云:“无所偏向于外,视犹不视。”婴儿终日观看,是为“视”,但此“视”并不寻求对外物的认知,是为“不视”。《知北游》云:“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一汝视”再次强调了目光的纯粹专一,对居道合德而言,这既是工夫也是境界,而达此境界者的目光能够“瞳焉如新出之犊而无求其故”。“瞳焉”,成玄英云:“无知直视之貌。”“直视”即目光停留在所观而不游移,“无知”指不对所观进行对象化求索,是所谓“无求其故”。林希逸云:“犊之初生,未尝不视而何尝有所视,赤子亦然;无求其故,谓人不知其所以视者如何也。”牛犊有眼睛、会观看,此即“未尝不视”;但牛犊不知道亦不求索为什么观看,此时所观就不会成为牛犊的对象,牛犊也不会拥有关于所观的知识,此即“何尝有所视”。林希逸之“未尝不视而何尝有所视”即宣颖之“视犹不视”,共同指出了《庄子》式的观看并不追求关于对象的旁观式的知识,而是追寻以婴儿、牛犊为象征的初始而质朴并且充满生命力的存在形态。
综上所论,从以“道”超克“形”,到以“体”通达“道”,再到对婴儿、牛犊目光的赞赏,《庄子》在存在论、方法论、生存论等方面都展现出了独特的旨趣,而这些旨趣无疑都关联着《庄子》独特的视觉经验及其对视觉的独特态度。《庄子》始终对眼睛所具有的对象性认知功能保持警惕,也不以“形”这一视觉对象为事物的本质,《庄子》重视的是眼睛之于生命的意义,以及生命本身不可形式化的向度,由之相视这一交互性的视觉经验得到重视,婴儿等虽不具认知功能却展现着初始生命力的目光受到青睐。然而,婴儿总会长大,在成人社会,婴儿式的眼光如何具有现实性?《庄子》对此没有直接讨论,不过,依循《庄子》的思路,借其“不得已”的讲法,或可如下回答:无论成人的目光如何不可避免,都不能由其不可避免而确证它的正当性,那终究是一种“不得已”,在“不得已”之中,婴儿的目光始终可以作为一种典范,对有志于“道”者提供精神引领,为在世者提供另一条观看世界的进路。
自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以来,经验被视作科学知识得以可能的前提,这似乎拔高了经验的位置,但实际上剥离了经验的精神性,使得各种具体经验不再成为哲学关注的对象。然而,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经验就保持着高度精神化的状态,它并非等待知性统摄的一片杂多,而是自始就包含着普遍性,并且深度参与着哲学形态与哲学品格的塑造。值得注意的是,重视经验并不意味着将哲学还原为经验,更不意味着哲学研究就是经验研究,而是说:从经验出发,各哲学传统的独特性与内在义理将能在源头处得到澄清。本文对《庄子》视觉经验的探讨正是基于上述理念的具体研究。整体来看,本文所谈到的视觉经验都不是私人经验,无论旁观还是互视,无论成人观看还是婴儿观看,都是人类的共同经验。只不过,在不同的文明进程中,视觉经验的不同类型所受到的重视并不相同,这种不同对各自哲学的展开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庄子》而言,对“观化”、相视、玄冥的重视与对“相”、旁观、光耀的警惕以及对婴儿式目光的赞赏构成了《庄子》视觉经验的完整面貌,这些内容既勾连着《庄子》在存在论、方法论、生存论等诸多层面的内在义理,又使《庄子》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尤其是相较于视觉中心论的独特性。从更广的视域来看,先秦诸子及秦汉以降的哲人无不重视日常生存经验,如孟子之孺子入井、阳明之南镇观花等,这些经验都具有普遍性而非纯私人感受。更为重要的是,哲人们使这些经验高度精神化,既展现着自身的哲学倾向,也形塑了中国哲学的整体品格。对现代研究来说,如果能进入古人原初而独特的生存经验,中国哲学的内在特征将得到基源性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化也会由之获得新的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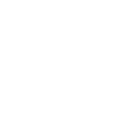

@HASHKFK